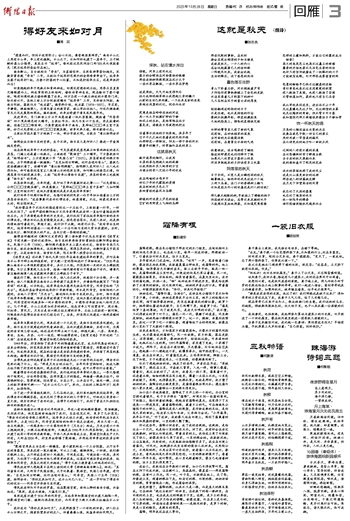■彭建华
霜降有根。根在朱公塘院子那老宅的木门缝里,在垅坑稻田土埂的狗尾巴草茎上,也在我心里。每年一到这时候,那根就动一下,引着我往旧时光里走,往乡土里走。
多年前的木门还在响。天刚亮,“吱呀”一声,尾音绕着门轴转,像老朋友拍我肩膀。我踩着晨露去野地里,赴霜降的约。地上的薄霜,细得像老天爷撒的盐末,踩上去软乎乎的,鞋底一响一响,是霜降的根在土里呼吸。田埂边的狗尾巴草沾着霜,风一吹,簌簌落在鞋窝里,凉丝丝的。稻茬顶着霜花,在晨光里泛白。老井沿的霜也脆,水桶一丢,“啪”地碎成沫子掉进井里,像是给这根添了点清冽的滋味。远处炊烟升起,奶奶的声音从村口来,带着霜的冷,却暖得能焐热耳朵:“华仔,回来吃早饭咯!”
奶奶总说,“霜降打霜,谷满仓”。这话在朱公塘院子里不知传了多少辈。小时候,奶奶总爱牵我手去田土里,她手上的纹路比田垄还深,指节粗得像老树枝,兜里总揣着温热的烤红薯。拔萝卜时,她将烤红薯递给我暖手,自己则蹲下身,指着萝卜说:“霜是给萝卜盖的薄被,化了就更沉实,是老天爷喂的补药。”我不懂,只记得拔出的萝卜叶子上,霜花一闪一闪,像撒了碎星星,风里都是甜味。奶奶用袖口擦擦瓷白的萝卜,咬一口,脆甜,再塞到我嘴里。我咬一口萝卜吃一口烤红薯,顺着喉咙下去的两股甜,就像在我心里扎下了无数的小根须。
后来走南闯北,才知道家乡的霜最温和。不像北方的霜风刮脸生疼,也不像南边的霜娇气,风一吹就散。家乡的霜,落在皮肤上,凉得清醒,不刺骨,像奶奶的手,轻轻抚过脸。可再温和的霜,也抵不过人生的寒。1995年霜降前,家里遭了变故,小家塌了半边天。那阵子,我总在半夜惊醒,月光像霜,冷冷地洒在空床上。想起要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就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一天清晨,我坐在田埂上,盯着霜花发呆。土冻得邦邦硬,脚踩上去,没了知觉,日子也像这冻土,心里的根,好像都要冻断了。
冷不丁想起奶奶的话。她走了好些年,声音还在耳边:“草被霜打蔫了,根还在土里,开春就又冒芽。人也一样,难事儿像霜,看着冷,熬过去就好了。”这时,我看见一株小草,霜裹着叶子,还透着点绿,细细的根须在冻土缝里,攥着一点湿土不放。心里忽然就暖了。再难,也得像这草,把根扎紧。也就是那时,我才懂了奶奶的话:霜降后的庄稼更瓷实,是霜催着根往深处扎;遭过霜打的人骨头更硬,是磨难让心里的根长得更壮。
如今在小县城高楼里,霜降成了日历上的一个标记。办公室的空调吹着暖风,电子日历弹出“霜降”,却闻不到一丝霜的清冽。下班路上,路灯照着玻璃墙,想起老家霜降的晨光,总觉得少了点透亮——那透亮里,藏着霜降的根,藏着乡土的气。可在湘南朱公塘院子的田野上,霜降还是农人的默契,是作物成熟的见证,是狗尾巴草的新妆。给老家父母打电话,父亲偶尔会说:“今年霜厚,来年谷子好。”听了这话,我就像又站在田埂上,闻到了霜裹着的稻米和果蔬的香甜,心里的根又颤了颤。
所以这些年,霜降必回老家,成了我的老规矩。这规矩,是给过去一个交代,也是给心里的根浇点水。回了家,我有时会在老宅边栽棵树,树苗从田埂边挖,带着老家的土。我怕这土离了田埂就没了劲儿,就像我怕自己离了老家,心里的根会枯。我踩踩泥地,土沾在鞋底,沉甸甸的,比皮鞋踩柏油路踏实多了。我坐在田埂上看霜化,听风吹,把钢筋水泥里丢掉的慢劲儿找回来。不用赶公交,不用赶材料,不用去菜市讨价还价,就看霜一点点化成水,渗进土里,看风把狗尾巴草吹得晃悠悠,心里的根就舒展开了。看着那树一年年长高,枝叶繁茂,我心里也跟着踏实,像自己也借着树的根,往乡土里扎得更深了。
这会儿,我就站在当年栽的小树前,如今已长得枝繁叶茂。霜在太阳下化成水珠,沾在嫩叶上,亮晶晶的,像星星——那是霜降的根,在新叶上闪光。风一吹,叶子晃,水珠掉在地上,没了影,却渗进土里,顺着树根往下走,和老宅的根、田埂的根、奶奶话语里的根,紧紧缠绕在一起,形成蓬勃的姿势。
我忽然懂了,霜降的根,从来不只是一根,而是庞大的根系集成。它在奶奶“熬过去就好”的话里,在我栽下的每一棵树里,在田埂的泥土里,也在我走过的难捱日子里。这根,是乡土的牵挂,是人生的韧性,是岁月给我的馈赠。就像这霜,打在身上是冷的,可它养的根,却能结出最香甜的果——是稻米的香,是萝卜的甜,更是心里的踏实,是根系的深厚。
霜降,明年我还在这儿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