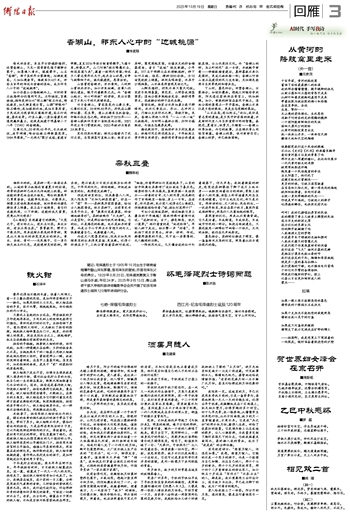■魏咏柏
湘西北的秋,是栾树一笔一画染出来的。山城的青石板路还留着夏日的余温,两旁的栾树却已迫不及待地披上秋装。碎金般的黄花尚在枝头摇曳,绛红的蒴果早已累累垂垂,这般争先恐后,不像草木,倒像土家族赶集的姑娘,把四季的好颜色都往身上堆叠。我立在小城街角,看它们这般热闹,心下却疑:这般的泼天富贵,究竟从何处修来?
《山海经》里便藏着它的根脚。“大荒之中,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禹攻云雨,有赤石焉生栾。”寥寥数字,劈开三千载光阴。原来这街头巷尾的寻常树,竟是从大禹治水的洪荒里走出的神木。黄本、赤枝、青叶——先民眼中,它一身尽纳天地五行之色,是能通神灵的药树。那赤枝,想必就是今日枝头这抹赤红的原咒。千年风雨吹打,神性渐褪,却把这血统里的红,熬得愈发浓稠了。
但这神话里的红,到底要落入人间。宋人陈亮写“不知几树栾团着”,妙在一个“团”字——栾树果序团团簇簇,恰似士人抱团清谈。秋日栾树下,当有青衣书生负手而立,看“蒴果灯笼悬碧落,碎金铺地映青衫”。栾树被唤作“大夫树”,未必是官阶,许是那份独对秋风的清挺。它的红,不是梅花的孤傲,也不是牡丹的富贵,而是士子心中那点不肯熄灭的灯火,既要暖着自己,也要暖着人间。
而这文人笔墨里的红,到底不如民间街巷里的红来得更直接、更泼辣。记得小时候在乡下,三叔公曾指着栾树对我说:“细娃,你看那树红灯笼挂起来了,山里的金牛快要出来耍哩!”这红就成了喜庆色。嫁娶时捡几串压箱底,盖新房摘一束挂梁头——神兽的玄奇、文人的风骨,到底都化作了百姓碗里一粒饭、身上一寸布。在老家,你问栾树,未必有人说得出《山海经》,但谁都能指给你看:“喏,挂红灯笼那个!”
可如今这满城栾树,谁还细数它身上叠压的千年魂魄?园林师傅叼着烟对我说:“这树好活,虫少,颜色鲜亮,秋天一道景。”他们看重的是“抗逆性强”。年轻人树下走过,抬头赞一声“好看”,手机拍下便匆匆离去。神话、诗词、传说,都像那蒴果的外壳,风干成一层薄薄的、无人翻阅的注释。
一阵秋风吹过,几片镶金边的红叶打着旋落下,悄无声息。我抚着皴裂的树皮,忽觉这栾树像极了脚下这片土地本身——血脉里淌着远古的神秘,骨架上刻着士人的风霜,面容上却洋溢着民间生生不息的暖意。它什么也没忘记,却只是不言。将神话的红、文人的红、民俗的红,一一收进年轮里,然后在某个秋日,轰然炸裂成满树绛云,照亮行人无意抬起的眼帘。
最深重的记忆,原来从不需要背诵。它只是活着,长成街道,长成秋色,长成城市呼吸的一部分。纵使名姓被遗忘,只要还能用一树绛红叩响每一个秋天,文化的血脉,就仍在无声地奔流。
暮色渐合,栾树的红融进夕晖里,像一盏盏渐次点亮的灯笼,照亮着从远古通往现代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