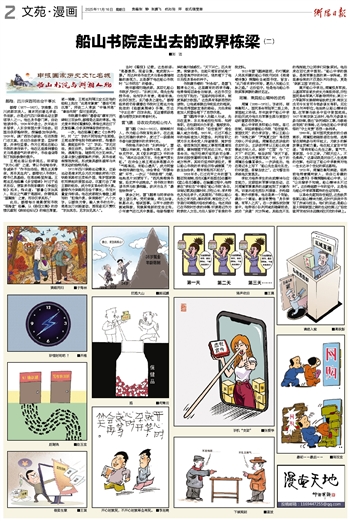■刘 洁
颜楷:四川保路同志会干事长
颜楷(1877—1927),字雍耆,四川成都双流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书法家,亦是近代四川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1904年中进士,次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习法政。回国后供职翰林院,授编修加侍讲衔。1909年,调广西协办新政,任巡抚衙门总文案,还创办法政学堂、监狱学堂,并亲任监督。作为王闿运在船山书院的亲传弟子,他在这座浸润着经史与笔墨香气的学府中,书法造诣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提升。
王闿运虽以经学闻名,却深谙“字为心画”之道,常以书法喻治学,告诫弟子“作书如治经,需先正其骨架,再丰其血肉”。颜楷初入书院时,楷书已具基础,但笔法略显拘谨。王闿运见他临摹《多宝塔碑》时过于追求形似,便取来书院珍藏的《争座位帖》拓本,指点道:“颜鲁公字如其人,刚正之气藏于笔画间,你需悟其‘屋漏痕’之意,而非仅学其形。”
此后,颜楷每日清晨便到书院“观海堂”临摹,从《祭侄文稿》的悲愤沉雄到《麻姑仙坛记》的端庄厚重,逐一揣摩,王闿运则隔三岔五在他的临帖上批注“此笔有篆意”“墨法可再沉厚”,师徒二人常就“中锋用笔”“章法布局”探讨至深夜。
书院藏书楼的“墨香阁”藏有历代碑帖三百余件,颜楷是这里的常客。他尤爱米芾的《蜀素帖》,常借出来在灯下反复临摹,分析其侧锋取势的妙处。
一次,他在临摹王羲之《兰亭序》时,对“之”字的不同写法产生困惑,王闿运便带他到书院碑林前,指着苏轼、黄庭坚所书“之”字说:“字无定法,贵在自然,如湘江流水,遇石则转,遇滩则急,随势而为方见神采。”这番点拨让颜楷豁然开朗,其书法逐渐摆脱拘泥,形成兼具颜体雄浑与米芾灵动的独特风格。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这场运动是清末民众为反对清政府将川汉铁路筑路权出卖给外国,维护国家路权而掀起的爱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颜楷作为保路同志会干事长,书写大量宣传标语。他在成都街头墙壁上题写的“拒借外债,保我路权”八个大字,以颜体为骨,融入隶书的古朴,笔笔如刀刻般遒劲,围观者无不赞叹“字如其志,见字如见其人”。
当时《蜀报》记载,这些标语:“笔墨激昂,观者云集,竟成街头一景。”而这种将书法艺术与革命激情相融的表现力,正是源于他在船山书院时“以书明志”的修炼。
晚年颜楷归隐成都,其回忆船山书院岁月时曰:“东洲三年,得先生指授书法,始知字外有意,笔端有魂,此非仅技艺,实乃修身之道也。”颜楷临终前仍珍藏着在书院时王闿运为他批改的《临颜真卿碑》手稿,页边“守正出奇”四字朱批,见证着那段笔墨与理想交织的青春时光。
雷飞鹏:诗政双优的船山传人
雷飞鹏(1863—1933),湖南郴州人,作为船山书院首批弟子,在这座依江而建的学府中,度过了一段浸润书香与家国情怀的求学时光。
书院每月举办的“东洲诗会”,雷飞鹏从未缺席。他善作七律,尤长于咏史抒怀,其《登东洲望江》中的诗句:“湘水汤汤流万古,书生意气贯长虹。”在诗会上被王闿运亲笔圈点为“气格高远,有船山遗风”,成为同窗争相传诵的佳句。诗会常设“即景命题”环节,一次以“书院秋柳”为题,他构思片刻便写下:“西风拂柳拂书窗,经史声中送晚凉。”将书院日常的读书声与秋景相融,获评为当月“最佳咏物诗”。
课余之时,雷飞鹏常与同学结伴登上望江亭,凭栏俯瞰,湘江如练,帆影点点,畅谈国事。从甲午战败的割地赔款,到康梁维新的变法主张,少年意气在江风中激荡。他曾指着对岸的衡州城感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辈读书,岂能只埋首故纸堆?”这些登高抒怀的时刻,悄然埋下了他日后投身革命的种子。
书院藏书楼的“时务阁”,是雷飞鹏常去之处。这里藏有的西学书籍,他常借阅回斋舍后细读,还在书页空白处写下批注:“坚船利炮非根本,制度革新方救国。”这些具有革新思想的读物,让他逐渐跳出传统经史的框架,开始思考国家变革的路径,为后来秘密加入同盟会埋下了思想伏笔。
雷飞鹏考中举人后踏入仕途,先后在直隶、东北等地担任知县、知府等职,在任期间兴办学堂、整顿吏治,将船山书院习得的“经世致用”理念融入地方治理。1905年,已过不惑之年的他秘密加入同盟会,利用官职之便为东北革命党人传递情报、掩护活动,曾因策划反清起义事泄而遭清廷通缉,辗转隐匿于民间近三年。辛亥革命后,他历任奉天省民政司佥事、吉林巡按使署顾问等职,致力于稳定地方秩序,其间仍坚持研读经史,常以船山书院的求学经历告诫僚属“为政当如治学,需有根柢而不泥古”。
1928年冬,已过花甲之年的雷飞鹏回到湖南,担任《嘉禾县图志》总纂和《蓝山县志》纂修。在编纂过程中,他特意在“学校志”中增设“船山书院”条目,详细记载其创建时间、历任山长、学术特色及知名学子,尤其提到:“书院以船山先生之学为宗,兼采西学,育经世之才。”字里行间满是对母校的感念。他还将自己在书院时抄录的诗稿、听课笔记作为附录收入方志,为后人留存了珍贵的书院史料。
1933年雷飞鹏病逝前,仍叮嘱家人将其所藏的船山书院刊刻本《湘绮楼诗集》捐赠给当地图书馆,留言:“此乃吾求学时所珍,愿后人知船山文脉之盛。”这份坚守,恰是他与船山书院深厚渊源的最好见证。
周斓:兼具船山精神的武将
周斓(1892—1952),字叔祁,湖南衡阳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爱国起义将领。早年就学于船山中学的经历成为他日后军事生涯与爱国行动的重要思想源头。
船山中学前身即船山书院。虽已改制,却延续着船山书院“经世致用、爱国忧民”的办学宗旨,常以王船山的“华夷之辨”“严夷夏之防”等思想为核心开设讲座。周斓是这类讲座的忠实听众,主讲老师常以王船山抗清事迹为切入点,剖析“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每当讲到“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时,台下的周斓总会攥紧拳头。一次讲座后,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船山先生虽处乱世,仍怀家国,吾辈当效之”,这句誓言后来被他反复提及。
学校为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与应变能力,定期组织军事训练活动,这对周斓军事素养的启蒙起到了关键作用。训练内容包括队列操练、步枪瞄准、野外侦察等,他总是第一个到场,最后一个离场,教官称赞他“身手矫健,有军人之风”。在一次模拟攻防演练中,他带领小队利用地形隐蔽前进,成功“突袭”对方阵地,其临危不乱的指挥能力让同学们印象深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船山中学的操场,是我军事生涯的第一块阵地,那里教会我的不仅是队列与射击,更是‘保家卫国’的担当。”
离开船山中学后,周斓投身军旅,从基层军官逐步成长为高级将领,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教导师师长、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无论身处何种职位,他始终以船山精神自勉,在军事与政务中坚守爱国底线。1937年南京保卫战时,他作为参谋长参与防御,提出“依托城防工事,与敌巷战到底”的策略,这与他在船山中学领悟的“守土有责”思想一脉相承。
1949年,面对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周斓拒绝随部退往台湾,选择留在湖南参与和平起义,为家乡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他在起义宣言中写道:“吾湘有船山先生之教,重气节,爱家国,今日之举,乃顺天应人,不负桑梓。”这番话既是对自己人生选择的注解,也印证了船山中学教育对他一生长达半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1952年,周斓在衡阳病逝,临终前他特意嘱咐家人,将自己珍藏的《船山遗书》手稿捐赠给船山中学,以“让后辈学子知晓,船山精神永不过时”。这份跨越数十年的坚守,正是他与船山中学深厚羁绊的生动写照。
从革命先驱到治世能臣,这些政界栋梁以船山精神为舵,在时代洪流中书写了赤诚与担当。他们的足迹,是船山星火照彻家国之路的生动注脚,让“经世致用”的校训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