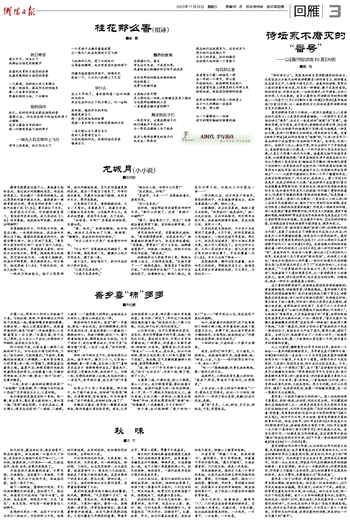■朱仕鹏
白露一过,鄂西北小村的山风就换了口音。它把松脂、柴烟、牛粪和晒过太阳的柿子皮搅在一起,像粗陶罐里新捣的辣酱,先辣后甜,一路从山梁灌进鼻孔。我踩着布鞋回村,鞋底“咕滋”一声踩破露水,心里跟着冒出一句土谚:“白露见霜,柿子发光。”果然,左山右山一片赤红,仿佛谁把夕阳掰碎,挂在枝头当灯笼。
村口的坎子边,从前站着一棵两人合抱的柿子王。爷爷也说不清它的年纪,只说:“我吃奶时,它就吮露水。”开春时,黑魆魆的枯枝像老人伸懒腰,一夜间冒出绿豆大的芽苞;再一夜,叶掌翻飞,绿荫能盖住整条土路。盛夏午后,树荫里摆四块被屁股磨得发亮的青石,石面渗着人油、汗碱和旱烟焦油,太阳一晒,散出一股子“社味”,呛鼻却踏实。
“三叔,再讲一遍柿树成精的神剧!”“成啥精?它要是精,早一脚踹飞你们这些小屁娃!”笑声砸在石头上,火星四溅。
我们最盼的是落花后的小青柿。捡一颗,剥去青衣,露出碧玉般的柿心,拿竹签一插,“哧溜”旋成陀螺。大家趴在地上,鼻尖蹭土,嘴里念念有词:“一旋福,二旋禄,三旋寿……”旋得最久的那枚,会被供在石头神位上,像给山神递红包一样。
熟透的柿子也招风。夜里“啪”一声落地,摔成一朵红泥花。我们猫腰蹿出,捡到手先感到冰凉,再感到柔软——像握住一颗跳动的心。用袖口擦擦,轻咬一口,蜜汁顺着指缝流淌,糯得能把舌头粘住。吃多了闹肚子,我们就蹲在地头,听肚子里“咕噜咕噜”打雷,一边笑一边骂:“好吃的嘴,甜死鬼!”
那时,柿子树归生产队,再甜也得先公后私。春节例外。腊月二十八,父亲端一碗糨糊,拿一管大楷,在红纸上写下“喜柿多多在吾乡 福荫绵绵护后庄。”墨迹未干,被邻家二哥搬来木梯,贴到树干上。对联一贴,仿佛给老树披上红袍,也给我们披上一层底气:来年饿不着,因为有“柿”作靠山。
好景止于小学二年级暑假。那天晌午,知了嗓子喊出血,老柿树“吱嘎嘎”跪倒。木屑像黄雪,纷纷扬扬。队长举着斧头喊:“老干部要走,老柿树去陪,值了!”
我躲在石磨后,看年轮一圈圈滚成棺材板,眼泪混着木屑往肚里咽。夜里,父亲在残桩前燃三炷香,烟头像三粒不肯坠落的星。我问他:“树没了,年咋过?”他把烟锅往鞋底磕了磕:“树走枝不走,人散心不散。记住,柿子红时,咱们还得笑。”
山不转水转。生产队管辖的沈家沟、老张沟、草坊沟等像摊开的手掌,托起一兜兜红灯笼。最远的左家沟,开荒六百多亩贫瘠坡地,广种薄收,却养着上百棵牛筋柿、保满柿、灯笼柿。霜降前后,队里仓库“堆成山”——不是山,是红浪。妇女们码柿垛,像给土地还愿;男人们取几筐酿“柿子老烧”。酒出甑,空气里飘起蜜糖拌火的味道,熏得野蜂都醉了。
“娃,抿一口!”牛爷用铜勺舀半盅递我,“这叫‘红运当头’,你有口福,辣了嘴,甜了心头。”
打霜第二遍,叶稀光透,树上只剩果,漫山一片红。我们挎篮背篓,像收拾落日的碎瓣。姑娘们把最大的一枚别在辫梢,走一步,晃一下,像把太阳拴在发尖上。挑灯夜焙,土炕上铺一层柿饼,火塘里松柴“噼啪”炸响,母亲把篾席拍得“嘭嘭”响:“饼要翻身,人也要翻身,日子才甜润!”
除夕夜,会计敲铜锣:“每户柿饼一包!”“当——”锣声滚过山谷,滚成我笔下最红的韵脚。
如今,我踩着水泥路回村,坎子边新栽的小柿树才碗口粗,却学着老树,把枝丫探进蓝天白云。我蹲下身,把从城市带来的半罐地铁风、半袋霓虹,统统倒进去:“你替我把这些养甜,再还给城市。”
小柿树不语,只递给我一片落叶当请柬。
夜里,全村吃“柿子宴”。灯火摇曳,人脸通红。我被推到场中央,端着酒碗,喊:“树在,山在,人在——咱们就得让柿子红一年,再红一年!”
“吼——”酒碗相撞,淡黄色液体溅起,像一场阴天的日出。
返程那天,三婶往我背包塞七层柿饼:“最底下那层,等城里下雪再吃,记得想家。”
火车启动,山梁上的柿子树排成“人”字,像给天空写情书。我咬一小口柿饼,甜味炸开——原来乡愁不是愁,是糖;归途不是途,是根。
喜“柿”多多。人在,树在,岁月在,甜味在,于是,希望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