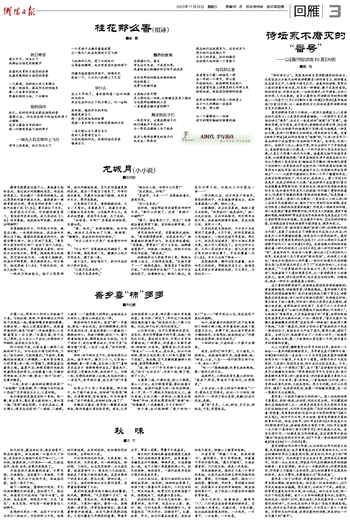■聂 泓
“诗到语言止”。高密度的语言是诗歌建筑的炼金石,没有这些石头就无法构筑诗歌殿堂;诗到语言止,指诗意生发在语言之中,又游离于语言之外。读聂沛的诗歌,常常让人感到诗意扑面而来,而且有一种精致、臻于完美的感受。他的诗灵动、回荡与延伸,一如林间清风;水中游鱼,让你心有所得,又无法拿捏。我且以聂沛40年诗歌创作的部分精选——刊登于11月2日《衡阳日报·回雁》头条的《聂沛短诗选(10首)》为例,以一斑窥豹的方式来谈谈聂沛诗歌的语言艺术及精神原乡。
聂沛诗歌语言的三大特征:一是强大造境能力;二是潜在的内在张力;三是强烈的情感磁场。一代国学大家王国维论诗之“境界”,论点之一就是诗的“造境”与“写境”。造境和写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做到泾渭分明,但各有侧重。窃以为诗歌中的造境高于写境;因为造境是一种复合之境,是诗人对事物充分体悟后,得来的语言之境。来看《树林子那边》是如何运用语言“造境”的。“父亲/好多年了/我在树林子这边望你/你在树林子那边”。俗话说:艺高人胆大。这种开门见山,看似平常,却为全诗打下了牢固的基石,直接营造出核心之境;是一个时代我和父亲生存状态之境;又是父子两辈人的代沟之境。接着通过细节的描写来呈现,以语境营造诗境:“青草歪倒的泥淖中满是鸟的爪印/你从干燥的小径走到地里/锄柄在手中颤抖/烟和潮气损害了你的肺叶/在黄昏我似乎总能听到一阵阵喘息和咳嗽/赶紧用书本遮住耳朵/因为我羞愧于自己/没有跟你学会怎样挖土”——一个被劳作磨损的父亲和一个年少懵懂的学生,在语言环境的烘托下,呼之欲出,跃然纸上。第二节的8行是尾声,也是全诗的出口之境:“我在树林子这边望你/曾与你在晚餐桌旁默默对饮/沉重的生活/使我们变得愈加熟悉和无言/我知道你呼吸里长久的疲倦/你对微小事物的执着劲儿/你漠然中隐藏的深情/常使我彻夜难眠。”还是隔着一座林子,这是一座诗人无法搬动、一直压在心上的山林;诗人在经历风雨磨砺之后,增加了对父亲的怀念和理解,甚至还对他身上特有的品质肃然起敬!即使是心理描写和抒情,诗人也是通过“餐桌旁默默对饮,呼吸里长久的疲倦,漠然中隐藏的深情,彻夜难眠”等这些生活中的具体形态来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深深怀念和崇敬。完全摒弃平面化、空泛化的抒情俗套,让诗歌在语言的具体场景中获得重生、境界和张力。
美国诗人简·赫斯菲尔德的“秘密二种:论诗歌的内视与外视”,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诗歌语言内在张力之所在;内视是内心世界精微的披露,诗是在内心世界的独步。聂沛的诗歌语言究竟有怎样的内在张力?以什么样的方式独步诗歌中的内心?我们来看《大雨》。这首诗题与诗的构思就潜伏着一种无形的张力,名为《大雨》,诗人却巧妙地避开了“雨”,直接写雨中、雨后的人和事,借以进入《大雨》的内心世界,这就是诗人自己常说的“侧向思维”。此诗有三大悬念:“谁也不知道他内心的风暴;一丝记忆和遗忘双向的微弱光亮/让怎样虚无的花儿开了?”“没有雨伞的人,才不会被淋湿。”“只有勇猛的风/在县城以外,更广阔的田野上面”,给读者留下大量的想象空间,让一首诗获得巨大的潜在张力。诚然,诗不是说明书,也不是生活的注释。归根结底,她是一种艺术,就像悬崖上的树。
在大量的诗歌阅读中,我渐渐发现诗是有情感磁场的;情感磁场越强,诗核越紧密,诗意就越浓。聂沛诗歌又有怎样浓烈的情感磁场呢?我们来读《孤独只剩下骨头》,诗歌要表达的是孤独,诗人如何让孤独凸现呢?此诗诞生伊始,骨头就成了核心意象,同时诗人深知只有骨头是不够的,再辅以铁皮鼓,这样孤独不但变硬了,且有了令人不安的声音。把孤独置于“山脉已低得像地平线的群蚁/平原阔大”,让孤独与“黑夜将至,天空准备投宿于此”并置,这样的孤独因此显得更加尖锐和无助,小如一根肋骨。“看不见落日/也摸不着微微颤抖的寂寥”这是怎样一种孤独?孤独得只剩下孤独。“只有一缕星光,烛照尘世的力量”孤独的出口也是一首诗的出口,孤独至此几乎成了虚无,像爱之痛,痛到了最后。全诗12行,孤独像长出了一双有力的手,一把抱紧你。疼痛和无助,像一只玻璃杯从高空落入平原,经历着无声的恐惧和折磨。
以上10首诗,横跨聂沛40年写作的30年,朝向同一个地址——聂沛诗歌的精神原乡。多年前发表于《衡阳日报·回雁》副刊的《我一直在给一个乡长写信》就是聂沛诗歌精神原乡的一个缩写,乡长是中心意象。诗歌中的乡长是乌有的,又是诗人坚信存在的,他不在过去就在未来。乡长,在诗中只是一个理想之“象”,这个“象”在诗意的流动中还是可以触摸和勾勒的:“那卓绝的坚守中无言的大美/孩子都是瞬间美学家;诗人垂垂老矣/但仍能就着落日豪饮大江而不醉”,乡长由真、善、美构成,一首短短的10行诗,诗人写得如此荡气回肠,又极其悲怆。用乡长作题,为什么不用村长、镇长?也是有讲究的,就像一件细腻的瓷器,差一分一毫都不足以成精品。
聂沛是一个极有天赋和才华的诗人。有人说他的诗源于聂鲁达、圣琼·佩斯,应该有,但远不是全部。作为朦胧诗潮之后崛起的诗人之一,他更多的是里尔克式悲悯与东坡式旷达相结合的、无问西东的透彻:“马匹仍然优雅地走动着/思想着,用高贵的身世/包容对这个世界的愤怒”(《银子的月亮》)。他对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哲学美学都有丰富的积累和沉淀。他成名较早,1985年在《诗刊》头条发表处女作《歌唱黄河》后,被破格录取为国家干部,1986年出版第一本只有17首诗的小册子《季节河》,却引起较大反响。这里没有炒作,一切都是因为风的缘故,其后便源源不断地“飘出”他标志性的系列长诗,如《下午是一条远逝的河》《傍晚》《蝗虫》和《十一月的风》等。
聂沛诗歌创作分两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的宏大叙事,采用整体象征、逐步意象感发的艺术策略和方式,以内在的精神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转变到90年代至今的“深度现实写作”。作品侧重于关注生活日常,透明度也不断提升。但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对内在的精神世界的挖掘和探索一直没有停歇。他不止一次跟我聊过:所谓深度现实,即用第三只眼看人生和世界,在已知的庸常中发现未知的神奇。我大为赞同,更愿意称之为“深水观鱼”。
聂沛是一位十分率性、举重若轻的诗人。手下诗句常常呈现出精致、经典的色彩。他本是一位肢体残疾人,2017年突发脑溢血后偏瘫。苍天惜才,让他活了下来。病愈后,他常常坐着电动车到处跑,活力犹在。他已生活无忧,唯一放不下的还是诗歌。就个人才华和诗歌质量而论,在国内,把他放在一流诗人行列,毫不逊色;与其说聂沛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诗人,不如说生活和工作在小县城长期被忽略。当然,他并不在乎这些,踽踽独行,只为写出一首又一首好诗。不管时光如何流逝,我深信聂沛的诗歌,将是诗坛一个永不磨灭的“番号”。